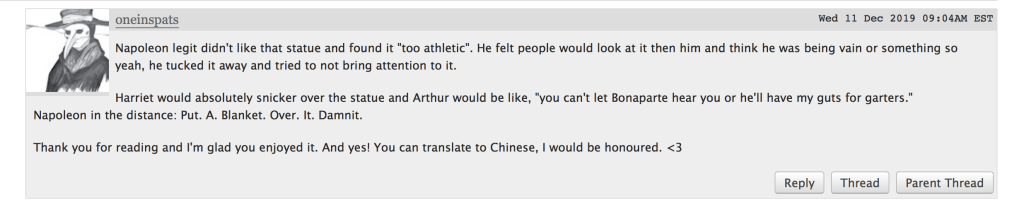
卡诺瓦创作的拿破仑雕像几经辗转后到了威灵顿手里,目前仍藏于伦敦阿普斯利府

它太健美了——拿破仑试图解释这一点。他反复解释。它的天职是展现本质,而非严格真实,但它没有履行天职。事实上,本质本身也是真实的一种形式。它是相对于外在的内在真实。
这玩意儿既不能展现本质,也不能展现真实。
“我不知道,我认为它给楼梯间增添了某样东西。”阿瑟坐在图书馆里,他穿着借来的家居袍。屋外在下雪。
“增添了尴尬。”拿破仑打断了他。
“只有你认为尴尬。”阿瑟拘谨地回答。
“我没有!”
“你有。”
拿破仑瞪着他。阿瑟微笑。他们陷入僵局了。自从一周前阿瑟来伍德福德,僵局就一直存在。这都怪姬蒂,因为是姬蒂让某个脾气肯定暴躁的皇帝得知臭名昭著的卡诺瓦雕像最终落入他们手里。拿破仑问姬蒂:于是你们把雕像放进屋子里间,并给它遮上一块布?
他是在偷偷摸摸地调查信息。
姬蒂没有察觉到做客的皇帝正愈发担心,她说:“哦,没有,它在前厅。我们得加固地板。”
妻子让他和拿破仑陷入僵局,虽然阿瑟对此感到气恼,但她说要加固地板时,当时波拿巴的表情值得一看。这是阿瑟第一次、他怀疑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表情。一生一度的机会难以言表。
“你知道它是礼物,对吧?”
拿破仑宣布他不在乎。他这辈子收到过很多礼物,认为没必要展示所有礼物。
“是摄政王的礼物,”阿瑟澄清道,“如果你不是同他地位相当的君王,想藏起他的礼物就有点困难。”
拿破仑盯着他。就算是教皇送的又怎样,他的感受也不会改变。那雕像是不必要的创作。卡诺瓦让他如此悲惨,此人应在光天化日下被枪毙。
“我在巴黎时听说,”阿瑟继续道,“约瑟芬似乎喜欢它。”
“喂——”
“它并不糟糕。”
“它糟透了。”
拿破仑发出噪音来表达不满。他开始阅读《泰晤士报》,报纸遮挡了他的身形。他不时嘟哝几句,抱怨粗鲁的英国人以及关于英国人的愚蠢行为和虚伪友谊的连篇累牍的报道。阿瑟任他自寻烦恼。
是的,雕像是有点过头了,它当然不符合阿瑟的品味,但摄政王如此热情,以至于他觉得有必要展示它。也许前厅是有点正确的选择。他稍微挪挪,开始缓缓沉下身体,平躺在沙发上。
壁炉架上的钟滴滴答答地走动。风雪敲打百叶窗。在这种天气下,阿瑟根本不可能马上出门。屋外所见只余白色和近处的事物的灰色阴影。风在狂嚎怒吼。钟在滴答作响。拿破仑翻了一页报纸。
“你知道的,它不是要让你难堪。”阿瑟终于开口。他平躺着,抱着一只枕头。另一只枕头盖着他冰冷的双脚。
“我的反对纯粹是美学上的。”
“我想我明白你为何耿耿于怀。”
传来沙沙的报纸翻页声。
“我真的不能搬走它,”礼貌的停顿后,阿瑟接着说,“它太大了。”
“拿块布遮住它。”
“我不会给前厅的雕像盖上布,不管身为雕像的你多么一丝不挂。”
传来表达不满的噪音。
“摄政王会非常失望。”阿瑟继续说。
拿破仑哼了一声。
“姬蒂会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拿破仑压低嗓音抱怨,阿瑟认为最好还是不要问他说了什么。
“拿块布遮上会很奇怪。我还要在那儿宴请或招待伦敦社会最重要的人。”
“耶稣哭了。[1]”拿破仑用科西嘉语说。
“噢,冷静点。”阿瑟用英语说。
拿破仑发火了。阿瑟坐起来,朝他扔了一只枕头。它落在书桌上,弄乱文件。拿破仑放下《泰晤士报》,他先是看看枕头,然后抬头看阿瑟。
“我没允许你扔枕头。”他指出。
“你在发无名火。”
“我没有发火。”
“你把这事看得太重了,严格意义上,你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又不是你远离祖国和家人,被所有人盯着观赏,然后发现那个永久流放你的家伙在自家门口摆放你的裸像。我可能得补充一句,那家伙不止摆放我的雕像,也摆放我,因为我也是展品。雕像又没有提醒你,他们正拿你的失败四处游行炫耀——”
“那雕像太大了,没法举着它游行炫耀。”
“对着欢天喜地的人群炫耀,正是这帮人恢复了堕落的专制君主制,它只会害了法国。雕像又没有提醒你,别人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
阿瑟扬起一边眉毛,他的表情在说“真的吗”。拿破仑抿紧嘴唇,他把枕头推下书桌,又缩回报纸的遮蔽之后。
“我的确说过,雕像不是要羞辱你,”阿瑟澄清道,“我解释了它到底是什么。”
“那不是重点。”
“好吧,但我不会移走它。你知道它有多大吗?”
拿破仑快速翻动报纸,阿瑟认为此举是想说“那也不是重点”。
“就算你想要道歉,我也不会道歉。”
“我为什么想要道歉?”他突然说。
“以防万一你认为我错了,”阿瑟澄清道,“我要说,我没错。”
“哦,没有,”传来嘲讽的声音,“你完全没错。”
阿瑟认为今天他受的讽刺和伤人的瞪视已经够多了,他拾起书,说如果拿破仑决定做个文明人,他可以来桌球室找他。或许他关门的动作太粗暴了,他听见有人在大声抱怨英国人。
4点半。这时桌球室的门被推开,先进门的是咖啡,然后是拿破仑。他端着两杯咖啡,所以这是求和的表态。他一脚带上门。
“我拿了咖啡。”拿破仑说。他把咖啡放在桌上。阿瑟坐着,身上裹着厚毯子,他没有回答。“现在轮到谁不理智了?要我说,这都怪天气,它让咱俩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野猪。趁热喝吧。”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贝特朗和蒙托隆的孩子们在大厅楼梯跑上跑下的动静,以及随后传来的大球滚动的声音,它淹没了尖叫的笑浪。
“至少有人玩得高兴。”阿瑟说,他放弃了,决定加入拿破仑,他仍然肩披毯子。“我没有撤到一个好房间。”
“没有,我想寒冷会迫使你投降,但我想起来了,你比我更适应寒冷。”
“拿破仑。”
听到他叫他的名字,拿破仑来了兴致。
“8月热浪时你也点火,”阿瑟的语气像引火物一样干巴巴,“你总是觉得冷。”
他露出了大大的微笑,那是足以改变天气的微笑。当然了,一切就是这样结束的——拿破仑揪他的耳朵,用英语说他是荒唐的人(他用小舌音发r音,用法式发音念元音[2])。阿瑟问一切是否安好,拿破仑说目前来看尚可,这是阿瑟所能期盼的最好结果,于是他接受了。
“你允许我回图书馆吗?”他问。
“你是自我放逐,韦尔斯利,”拿破仑轻拍他的鼻尖,“不过没错,我允许你回去,不然你会死在这。我们不能让你裹着毯子在大厅里乱转,你像是某个老国王巡视领地。”
“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
“我们不能让你死。阿巴思诺特夫妇[3]会伤心的。”
“只是阿巴思诺特夫妇伤心吗?”
拿破仑推着他进入图书馆,关上身后的门。他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关爱的神色:“别得寸进尺。我给你带了咖啡。我要送给你一块非常大的布,你知道该用它做什么。”
他们坐在壁炉前的地板上,身边围着枕头和太多的毯子。拿破仑取了一张毯子,盖在阿瑟的脑袋上:“我在给你示范,这样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毯子下的阿瑟压低声音,抱怨道他会看看他能做什么。波拿巴能友善地丢开这个话题吗?已经一周了。拿破仑说波拿巴会看看他能做什么,他拽下毯子,拍拍阿瑟的脸颊,宣称他是好人。虽然他是英国人,虽然他倾向于让太多人观看那尊健美得过头的皇帝雕像,可他仍是好人。事实上,拿破仑会说阿瑟是非常好的人。阿瑟接受了这种说法,他再次平躺,拿破仑的腿压着他的脚。
“我想你也是好人。虽然你是法国人,虽然你倾向于对健美的雕像感到不必要的沮丧,可你仍是好人。”
“你想换个说法吗?”
阿瑟让自己说不,他很可能不会让他们陷入温和的僵局,而那种僵局或许是这世上最好、最正确的秩序。
[1] 在英语里这个短语有咒骂的意思,可用于表达不相信、不在乎。
[2] 法国人说英语时往往掺杂很多法语口音,比如文中提到的小舌音和法式元音。
[3] 阿巴思诺特夫妇是威灵顿的至交好友。有学者认为他们三人是柏拉图三角关系。